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丨字母榜,作者丨蒋晓婷
安东的一天从中午开始。他是一名编剧,30岁,宅在燕郊靠近潮白河的一间出租屋里,目标是5年内拥有一部有名气的剧本作品。“女儿”木兰是一只才7个月的渐层猫,性格闹腾,喜欢在爸爸断网工作的时候大摇大摆走过来踩键盘、挡显示器,直到安东把她抱到怀里,顺顺毛,木兰才会安分。
安东需要这位猫主子,“有个活物在身边,感觉会好很多。”
今年是安东北漂的第7年,做了4年互联网运营,3年底层编剧,在北京搬过3次家——从亮马桥到马泉营,再到隶属河北的燕郊地区,租房离城中心越来越远。而燕郊的一间大房只要1400元,有厨房有卫生间,这种价位,在北京城内买不到一个上下铺床位。
选择这个便宜房存在通勤问题,每周3次进城开会,路上来回得花4个小时,以至于疫情之后,他反倒如鱼得水,和木兰相依为命,宅得彻底。
安东渴望在一部高质量作品的编剧栏上看到自己的名字,哪怕只是参与,“一个小编剧只要参与过《大明王朝1566》这种制作,出去找工作,所有人就会另眼看待。”
2016年10月成为新手编剧后,安东的生活基本围着工作转,生活节奏全乱,睡醒就码稿,累了就睡觉,一日两餐只需要填饱肚子,为了赶项目,一度在办公室住了3个多月,“差点抑郁。”
尽管这3年多时间,安东待过的编剧工作室来头都不小。上一家编剧工作室有某香港大导演做合伙人,创始人老杜做了十几年编剧,资源丰富,哪怕在影视寒冬,项目依旧扎堆。
去年年底应聘进业内一家颇有知名度的编剧工作室——近两年佳作不断,豆瓣平均分都在6分以上,合作的明星包括杨洋、陈伟霆、李现。
然而在老杜那儿,安东参与的好几部剧本都是不入流的网剧,要么质量差,要么迟迟无法上映,名字署上也是丢人。
如今这家新工作室,强手如林,他从入职开始,就负责给一个逐梦演艺圈的剧本做扫尾工作,因为进入项目时间比较晚,更没底气要求添一个署名。
一
安东入行是误打误撞。
他之前一直在互联网行业,在一家中型公司当网络运营,工作被数据、获客量、获客成本、运营渠道等等填满,心里却觉得空落落的,没有半点成就感。
2016年年中,因为阑尾炎发作,他回湖北老家做手术,休养一个月时间。看着家乡的青山绿水,他每天反问自己:4年时间究竟做了什么?“做一份不喜欢的工作,每天通勤要坐2个多小时地铁,简直要疯。”
他决定辞职。
就业的十字路口,安东把一个个选择项列在纸上,第一个是编剧,其余都是互联网岗位——产品经理、数据分析等。
安东知道编剧不好干,他没接受过剧本训练,冲动来自于大学期间看到刘恒的剧本《菊豆》、《秋菊打官司》,对编剧产生强烈好感,“编剧是一个很牛逼的存在。”
“只想试一试”。抱着这个念头,安东在招聘软件上找到老杜工作室,投简历、笔试、面试。至今回想起来都觉得离谱,“我从来没看过剧本,笔试写得剧本格式都不对,工作室也要我。”
面试当天,安东敲定入职,“几乎毫不犹豫。”他想的是留下来看看情况,看自己适不适合编剧行业。丝毫没顾及老杜在待遇上的苛刻:每月补助1800元,不签劳动合同,没有五险一金,“能坚持下去就做。”
安东自信能很快上手,以前做运营时可以,当编剧应该也一样。
工作室的学习方法是跟项目。老杜不是编剧科班出身,十几年踏在国产影视剧狂飙突进阶段,一身本领纯靠剧组练出来,没有科班理论,方法就是把徒弟们扔进剧组实战。
入职刚几天,安东就被老杜外派去剧组改剧本。剧组导演是老杜工作室的合伙人。安东觉得,机会来了。
在横店一干就是4个月,剧组超负荷运转,安东生活作息全乱。白天跟着拍摄节奏走,凌晨2、3点等导演下戏,回宾馆一起修改剧本,动辄挨骂。被导演提点后,安东得彻夜改剧本。“刚入行什么都不懂,赶鸭子上架,很痛苦。”
不光导演脾气大,统筹、灯光、道具经常熬大夜,身体状态差,脾气也是一点就着。
拍摄现场阶级分明。网剧男主时刻前簇后拥,替身演员打完动作戏后,走路一瘸一拐,周围连个扶一把的人都没有。剧组供应的椅子也是主演专座,工作人员可以坐在道具箱,群演只配蹲地上。“那会儿冬天很冷,群演都坐在室外。”
剧拍出来后评分特别低,但安东觉得四个月时间不算白费,“算开了窍。”
在横店期间,工作室6个编剧集体辞职,安东回来后被动成为老杜的左右手。所有家当搬到公司附近的燕郊大厂回族自治县——北京不少影视工作者的大本营,房租只要几百块。吃的是政府支持的食堂,生活全围着工作转。
工作室的新人来了一茬又一茬,只有安东适应老杜的做事风格。每次剧本讨论会,都是老杜提创意、出点子,其他人充当执行人,不需要提任何意见,“在他脑子短路的时候给点思路就好。”
但要执行下来,拼的是强体力。安东每天固定要写几千字培养手感,需要熬夜赶项目,经常写到脑子恍惚,“当时做梦都梦见马上要交稿”;被查出脊椎侧弯,又腾不出时间锻炼,再加上北京气候干燥,经常会喷鼻血。
跟组的时候更难受。如果说在工作室写稿是创作,在剧组就是补锅。场景、台词、演员,谁都可以给编剧提意见,最后剧本改得面目全非。
编剧都不愿意跟剧组。一去剧组至少3个月,能住上快捷酒店还好,碰到抠门的草台班子剧组,需要好几个人挤在一个房间,每天吃得盒饭都特别差。剧组的事儿还多,会出现资方塞角色,服化道、剧本走关系,导演没权利决定男女主,拍摄画面只要能看就行。
碰上这种剧组,安东只能认栽。即便是师傅老杜,在资方面前也是毕恭毕敬,所有意见照单全收。哪怕修改意见和剧情无关,只是给演员档期让道,按要求删戏、加戏、改人设,或者配合植入广告等。
这3年来,安东能触到的编剧任务只有低成本网剧。尽管老杜经常在他面前打包票:写出好剧本,就可以上央视六套。
但3年过去,安东参与了N部编剧项目,始终碰不到央六的门槛。
他曾看到过希望。2018年6月,工作室接到了一个据说可以上院线的电影项目。老杜安排安东和一名女同事去广州跟组3个月。到了之后才发现,原剧本不能用,需要边拍一边写,每天忙得找不到北。
谁知到剧本结束阶段,导演想要潜规则女同事被打,项目随之告吹。
安东只能暗怪自己倒霉,碰不上大剧组,只能每次被草台班子折腾,“越是大导演越是爱惜羽毛,副导演聊戏都会开门。”
他最后也发现,师傅老杜在圈里打拼十几年,署名作品屈指可数,豆瓣评分一片灰。安东想在老杜这儿拿一个能立身的编剧署名,希望渺茫。
二
“不念师徒情的人,跟畜生有什么两样。”这是老杜的口头禅。
老杜信奉传统师徒制,安东工作3年,一直没签劳动合同。直到在老杜工作室待到第3年,才在同事的争取下签了一份项目协议,了解酬劳分配的细节:8万一集的戏,分到编剧手里,一集不超过1万。
在此之前,安东的收入除了每月1800元,偶尔会拿到一点剧本收入,由老杜裁定,偶尔1万,偶尔3万,平时还要倒贴车费,或者给老杜买烟。
到2019年8月,安东意识到不对劲,“快30岁了,还需要向家里人给钱生活。”
安东没有什么物质欲望。日常除了吃喝买衣服,爱好为0。期间甚至用光了前4年互联网工作攒下的几万积蓄。
“我起码自己需要衣食无忧。”思考了2个月,安东决定离职,跟老杜坦白:没法呆了。
老杜没有挽留,这么多年工作室新人来来去去,他从不留人。他的骄傲在于,总有人会因为编剧梦,来给他鞍前马后,唯一的要求是:能学到东西。“入这行的人都渴望成功。你不做,有的是人做。”
安东一直感谢老杜带他入了行,但客观评价这位师傅,他说:老杜没有能力,教徒弟的方法落伍。“老杜工作室是非常传统的学徒制。类似德云社郭德纲带学徒,但老杜没有郭德纲的能力。”
也是在老杜这儿,安东有了原始野心。
在此之前,安东说自己是个随波逐流的人,没有梦想,更没什么见识。
他出生于湖北荆州农村,父母没有文化,靠小本生意养大安东两兄弟,唯一的要求是要他好好读书,小时候的很多愿望被学习抹杀,没有兴趣爱好,努力考上一本院校,到大学选志愿的时候一头懵。
最终选择了汉语言专业,是因为小时候爱看书,小学能通读《水浒传》、《三国演义》,初三看懂了《基督山伯爵》。
等到大学毕业后去广州当出版编辑,很快意识到自己不喜欢。随后一路北上找工作,“发现自己原来的世界那么小”,直到在北京落脚,依然迷茫。
因为没有职业规划,安东被培训班的宣传砸晕了头,借了近2万网贷学习程序员基础知识,“想进互联网行业,赚多点钱。”结果程序员没当上,阴差阳错当上了互联网运营。
直到4年后,对运营工作产生厌恶,在人生十字路口,又误打误撞当上了编剧。
这一次,安东失去了选择权。
2019年下半年,父母拿出10万积蓄,催促安东赶紧买房定居,“随便哪儿都行。”他告知父母真相:之前有积蓄,但现在没了。
偶尔他还会担心,自己再在编剧行业干下去,会吃不上饭。
面对直面派采访时,安东骂自己离开互联网行业来当编剧是年少无知,偏离轨道。“如果当初继续做互联网,每个月至少1万多收入。进了编剧行业就是1800元。”
但他很快认清现实:想回也回不去。“互联网行业更新得太快。跟不上了!”
他只能继续在编剧这条路上走下去。
三
到了30岁的年纪,安东不敢再浑浑噩噩下去,他急需要一个署名作品。“编剧靠名气吃饭,只要有一部作品立身,路会好走得多。”
去年年底,安东应聘进一家更优秀的编剧工作室,不仅收入高了,薪资翻倍到8K,还可以接触精品电视剧剧本创作,离梦想更进一步。
师傅的标准自然也高了。老杜要求听话,新主编则要求创意,每次剧本讨论会都是一场头脑风暴,要想主题想情节,不管说得多离谱,都要畅所欲言。
这是安东第二次感到痛苦。“第一次是刚入行那会儿,什么都不懂,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
第一次剧本讨论会,安东的脸红了半场。新工作室做的是精品电视剧,要求高,节奏慢,周期长,每一个细节都要磨合,IP的主题方向筛选都需要长时间讨论,跟老杜那儿的工作模式完全不一样。“和同事差距太大,我就是做网剧的水平。
入职不久,主编让安东负责给一个逐梦演艺圈的剧本扫尾,参与时间晚,自然没有署名权。“署名权看参与程度,超过30%就可以争取。”
因为剧本要求高,这半年来,安东每天除了和同事、主编沟通,大部分时间扑在工作上。下午1点左右断网,享受精力高度集中的写作状态。偶尔会持续到凌晨4、5点,长期伏案写作催化出过劳肥,安东172厘米的身高,体重140多斤,体脂明显偏高。
尽管几次听说有青年编剧熬夜猝死的消息,他也没有任何补救的措施,“预感自己迟早会猝死在工作上。”他唯一的保障手段是给自己买了一份意外险和重疾险,求个安心。
但这样高强度工作下来,他的进度条依旧缓慢。
“有点吃力”,安东说。他需要从头学起。在此之前,他看的片大多是文艺片,喜欢的导演是黑泽明、库布里克,和这家工作室的风格——商业电视剧方向格格不入。
他要疯狂补充韩剧。“之前积累特别少。一场戏要达到某个场景,什么情形下该吻,别人是信手拈来,我要一点点研究,跟经典剧取经。”
看的剧多了,安东对国产烂剧都有了同理心。“看的时候觉得很烂,写的时候又觉得情节设置很牛逼。如果让我写,我还真不定能写出来。”
但在追梦路上,他的焦虑感如影随形。“编剧行业的淘汰率很高,很多人耗不起等不起,会主动放弃。”安东见过很多中年编剧,与时代脱节,拿不到电视剧机会,网剧没人找,烂片的盘子都接不到。安东唯恐自己会变成这样的人,“很难想象到时候该怎么办?”
而如果不被社会淘汰,安东需要加倍使劲,“35岁左右要有一部有名气的电视剧,类似《欢乐颂》、《陆贞传奇》这样的量级。”
他也想听父母的话,尽快买房安家。但编剧的工作限制他,不能离开北京。“家里什么都好,但编剧工作只能在北京这个环境里面发展。燕郊的房子又买不起。”
如今,他现在的心态也变了。偶像不再是刘恒,而是想成为于正这样的编剧明星。
“如果于正的人生没有抄袭这一环,非常符合底层编剧往上走的路。从编剧做到制片人,他有话语权,懂得重视剧本,从《延禧攻略》到《鬓边》,口碑都挺好。”
安东想成为“于正”。
他说:“爬到越高的地位,遇到的人就是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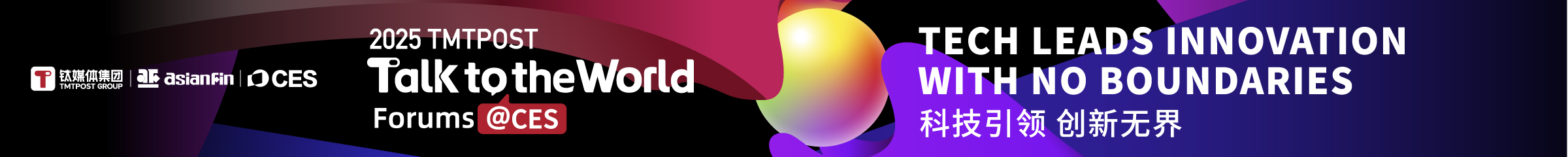
 快报
快报
根据《网络安全法》实名制要求,请绑定手机号后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