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钛媒体注:本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IT时报(ID:vittimes),作者 | 孙妍、李丹琦、徐晓倩,编辑 | 挨踢妹,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沈超(化名),一名95后顺丰快递小哥,中专毕业后在小镇做过汽车维修店学徒工,开过奶茶店,三年前离开小镇到上海谋生,主要目标是多赚钱,每个月他只关心到手工资能否过万,却从未登陆过自己的社保账户,也不关心雇主是谁。
沈超的母亲,一名70后小镇工人,她选择工厂的唯一条件是交社保,眼看到了退休年龄却还未交满15年,为了过上拿养老金的生活,她非常愿意自己继续交8年社保。
小镇青年为了高薪到大城市打零工,从没意识到社保和意外保险对自己的重要性,只想帮自己和家人改善生活,他们与留守老家的父母形成了鲜明反差。对父母来说,社保和稳定的工作才是最大的安全感,他们不想靠儿女养老。
直到这个寒冬,饿了么外卖骑手韩某猝死倒下,平台给出的2000元“人道主义补偿”刺痛了家属,也给同属于“平台-个人”这一雇佣关系的小哥们敲响了警钟。
上海顺丰小哥沈超第一次查询了自己的社保账户,弄清了自己的劳务合同是与宁波一家外包公司签署的,社保、医保也都缴纳在宁波,比起众包模式下的外卖骑手和快递小哥,有社保、医保却无法使用的外包员工尚属幸运。
不敢生病,不敢出意外,零工经济下的2亿劳动者,你们的社保在哪里?
01 2000元,85万
如果倒下的骑手有工伤保险,家属应拿多少补助?
倒下的韩某社交账号上,置顶第一条视频是一辆装有蓝色外卖箱的电瓶车,两个车把上用塑料袋做了防风手套,配乐是“我真的就在北京,就站在二环街上”。

韩某在社交账号上置顶的第一条视频
置顶的第二条视频是两个儿子唱着生日快乐歌,奶奶戴着生日皇冠,脸上洋溢着羞涩而幸福的笑。
曾经,山西老家的笑声抵消了北京街头的寒意,如今,家里的经济支柱终究抵不过寒意,满堂的笑声消失了。
韩某不是特例,2020年5月6日,也曾有一位武汉饿了么骑手肖刚在送餐途中猝死。
饿了么出于人道主义赔付2000元,保险公司根据投保金额1.06元理赔3万元,与韩某最初的赔付方式一模一样。
当饿了么在舆论压力下向韩某家属赔付60万元时,肖刚妻子要求的80万元工亡赔偿被武汉市黄陂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驳回,至今求告无门。
截至发稿前,饿了么也未对此做出回应。
“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平台用这一理由转移了所有责任,就像披上“隐身衣”般置身事外。意外发生时,众包模式下外卖骑手保障缺失的问题再次被撕开、放大。
韩某的意外猝死让这个不算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上有老下有小。
两个儿子是韩某在社交账号里的主角,大儿子读高二,小儿子还在读小学,所有的担子都将压向韩某的妻子。
饿了么给韩某家的赔偿从2000元涨到60万,是舆论发酵下的结果,如果没有舆论推动,还有多少意外纠纷案会像肖刚家一样被罔顾?

针对外卖员韩某猝死,饿了么的赔偿从2000元涨到60万元,图源:红星新闻、饿了么
如果每天被扣的3元不是拿来买了人身意外保险、付了服务费,而是缴纳了五险一金里的工伤保险,韩某和肖刚两家得到的赔偿,与60万会有多大差距?

骑手每天开工自动扣除3元费用,图源:饿了么客服
《上海市工伤保险条例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如果韩某与平台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标准是上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上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2359元,这意味着,如果当初外卖众包平台给韩某缴纳了工伤保险,他家人可以一次性拿到近85万的补助金,另外还有一笔长期发放的供养亲属抚恤金:由其提供主要经济来源、无劳动能力的父母、子女和配偶都能按一定比例获得。

《上海市工伤保险条例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图源: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官方公布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确定为847180元,图源:网络
根据《上海市:关于调整本市因工死亡人员供养亲属抚恤金标准的通知(沪人社规〔2020〕12号)》,按照韩某家的情况,如果他生前按每月5000元工资缴纳工伤保险,两位父母如满60周岁,两个儿子还未满18周岁,那么,四个人每人可以获得1652元的最低标准抚恤金。
如果交金基数为10000元,四个人则以此均分,每人每月2500元,直到孩子成年,老人过世。而且根据上海市规定,抚恤金还会根据全市职工平均工资和生活费用变化等情况适时调整。
对于失去主要劳动力的家庭而言,这是一笔长期稳定的保障。这还没有算上一笔丧葬补助金,相当于6个月的上海市上年度职工月均工资,那就是57480元。
02 6亿元去哪了?
平台、“包工头”和骑手的博弈。
但对外卖平台来说,包括工伤险在内的五险一金是一笔巨额支出。
饿了么App显示,其拥有300万骑手。美团《2019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则显示,旗下骑手总数高达399万人。


图源:饿了么、美团
庞大的骑手大军,如果全部纳入正式合同工,足以让两大外卖平台成为全球用工数最多的公司。要知道,全球用工数量榜首沃尔玛,也只有220万名员工。
韩某和肖刚生前跑外卖时,每天都会被扣3元,其中只有1.06元被用来购买人身意外保险,平台表示剩下的1.94元为服务费。
饿了么曾对媒体表示,平台上包括全职和兼职的月活跃骑手数为85万。
按照每位骑手每月至少做一单计算,平台一年收到的服务费约为1978.8万元,而如果每位骑手做满全年,则平台年服务费有6.02亿元。
这些服务费去了哪里?饿了么表示,3元服务费由饿了么平台代为收取,平台会再支付一部分费用,共同交给骑手所服务的人力资源商,委托其为众包骑士提供劳务管理和安全保障等服务,其中约定由人力资源商为骑士投保意外保险。
“趣活”是其中一家人力资源商,号称中国最大“包工头”,其主要业务是为美团、饿了么招募并管理骑手,该平台有3.99万名外卖骑手,其中1.3万名派遣到饿了么。

图源:趣活招股书
招股书显示,趣活的主营业务餐饮配送服务,2019年支付给骑手和管理人员的服务费占比达到84.5%,就每笔订单的运营成本而言,趣活已经为行业客户平均节省了约40%的成本。
“五险一金”恰恰占用工成本的32%-36%。根据上海社保缴费标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公积金的单位缴纳比例分别为:16%、9.5%、0.5%、1%、0.2%-1.5%和5%-7%。
趣活到底有没有为骑手交社保?天眼查显示,北京趣活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度为87人缴纳社保,控股的另一家上海趣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交金人数为4人。这两个数字与4万名骑手相差甚远。

北京趣活(总部)和上海趣活分别只有87和4人交金,图源:天眼查
即便在目前情况下,趣活仍是亏损状态,2017年、2018年、2019年净亏损分别为1397万元、4429万元、1345万元。

趣活连续三年亏损,图源:趣活招股书
如果再额外支出社保金,营收单一的第三方人力公司将面临巨大的压力。
平台将责任转移给“包工头”,“包工头”把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这是平台经济下的常规操作。
在“UU跑腿跑男端”的注册协议中显示,“跑男与UU跑腿平台仅存在一般的信息推送服务关系,并不存在劳动、劳务、雇佣关系。”
“任何时候,跑男从UU跑腿平台获取的利益(若有),不应当视为工资、新近及劳务报酬或类似收入。跑男应当自行委托UU跑腿平台购买商业保险,并自行承担旅行配送义务过程中的意外事故或责任事故的责任。”

图源:UU跑腿服务条款
在达达平台的注册协议中也显示,“在达达平台注册并为商户提供配送服务的实际承运人与达达平台之间并非劳动、劳务、雇佣关系。”
“您在配送服务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财产损害的,或造成第三方人身损害、财产损害的,应当依法向责任主体追究法律责任或独立对第三方承担法律责任,达达平台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在这场博弈中,骑手注定处于最弱势的地位,站在商业利益的角度,平台和“包工头”都很难主动跨出交社保这一步。
“现阶段只能从立法层面去保障骑手的社会权益,一是拓宽劳动关系的界定,将平台经济的用工者包括在内,二是不把他们定义成劳动关系,而把他们纳入到社会保险和工伤保险的范围内。”劳务纠纷律师张劼告诉《IT时报》记者。
人社部也曾表示,将适时启动《工伤保险条例》的再次修订工作,把外卖员、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新业态从业者纳入工伤保险制度保障当中。
03 对社保无感的一代
不敢生病、不敢出意外
和大多数不知情的骑手一样,众包外卖骑手王聪(化名)从没有研究过每天上交的3元到底派什么用场,“使用情况应该很复杂,只有撞到残废才能用吧?”王聪语气中充满了疑问,还不到24岁的他总能自己应付摔跤后的小伤小痛。
现实与小王的猜测基本吻合,外卖小哥、快递小哥要想获得意外险、医疗险的正常理赔非常之难,工伤则难上加难。

图源:东方IC
沈超在上海某顺丰站点送快递,但他签的却是宁波一家第三方劳务服务商,社保也缴纳在宁波。
“公司为了降低成本才交在宁波,谁敢生病,在上海,没有医保卡一盒感冒药都要50多元,双11连假都请不下来,很多人都带病带伤在送快递。”
在他工作的三年里,身边同事骑车摔倒受了伤,只要不到住院的程度,从没有人能认定为工伤,在他看来,站点主管卡了第一道口子,那是因为每个站点都有工伤指标上限,这与主管的绩效挂钩。
如果出了交通意外,只有工伤这条路可走,因为除了交在外地的社保,顺丰只为员工强制保了重疾险,每年每人需付的保费为169元,保障项目包括9000元重疾及疾病身故住院津贴,5万元附加疾病身故保险和20万元重大疾病保险,都不适用于交通意外这一高发的职业伤害。

顺丰要求员工强制参保169元的重疾险,不适用于交通意外这一高发的职业伤害
外卖小哥和快递小哥类似,大多分为两类,外包和众包。
像顺丰小哥沈超这样的外包员工大多与第三方人力公司签约,会缴纳社保,但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有社保但缴纳在外地,由于医保还未实现跨省结算,所以无法使用。众包模式下,绝大多数骑手没有社保,甚至没有雇主。
“不敢生病,不敢出意外”,接受采访的数十位外卖小哥、快递小哥几乎是同样的反馈,无论是否缴纳社保,大家的不安全感是相通的,对社保的无感也是相通的。
2020年,一男子应聘美团外卖骑手被站点要求自愿放弃社保,站点负责人表示双方是你情我愿的,放弃社保可以拿到更高的工资。

图源:广东台触电新闻
站点负责人的想法居然让大多数对社保无感的群体表示接受,“我来上海的目的就是赚钱,社保基本不考虑。”一位极兔快递员向《IT时报》记者表示,如果交金,到手的钱就少了,而且没想干快递干到老,“听说有交社保,但我没查到,也就放弃了,公司也没有买其他意外保险。”
圆通快递员薛强(化名)告诉记者,他跟圆通签订的是承包合同。每个月第三方公司都为站点的员工购买意外险,但金额和保单,他并未关注过。
相比其他快递,京东快递员的保障更为稳定。一位京东快递员表示,公司为他们缴纳五险一金和意外险,但他自己并不清楚保险内容,也不清楚缴了多少钱。
更有甚者,社保不翼而飞。多位上海的房地产中介告诉《IT时报》记者,前一家中介公司明明说帮他们在深圳交了社保,但当他们离职后发现,社保金查询不到,或许这笔钱从未缴纳过。
为何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都对社保无感?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解释,这种现状跟当下的社保缴纳制度、务工人员的年龄阶段、预期风险意识等有较大关系。我国社保属于各省财政独立支付体系,无法跨省参保,对于流动性大的农民工群体,劳动地点经常变动,因此在就业地缴纳保险的意愿较低。
同时,缴纳保险的意愿也与年龄有关。“我们对外卖员群体的调研发现,年龄在18-25岁、单身外卖员缴纳保险意愿明显低于25-40岁、已婚的外卖员人群。”孙萍认为,目前互联网用工多采用客单价,劳动保障程度低,获取短期利益的导向过于明显,未能有效培养从业人群的社会保障意识。
和王聪、沈超类似,2018年,李亮(化名)离开了曾经每月定期交社保的酒店工作,成为平台经济下茫茫打工人的一员。
“酒店经营状况越来越差,每个月到手只有五六千元。”外卖平台可观的收益让他选择舍弃掉稳定合同关系和社保。
之后的两年里,李亮没有去过一次上海的医院,大多时候他都不敢生病。李亮在飞驰的电动车上目睹过几次同行摔倒的画面,每当南方的梅雨季节、台风天来临,摔倒的风险几乎无处不在,他也会担心某天案发现场的主角就成了自己。
04 2亿人打零工
活跃者中90后与00后过半

图摄:IT时报
在送餐高峰时段,王聪是一名众包外卖骑手,在非高峰时段,王聪又去外卖摊点切菜、配菜,打一份工时费为25元的零工。每个月除了送外卖的收入外,还有3000元左右的切配工报酬。
结束配菜一般在早晨六点,而他必须赶在外卖高峰11点来临前接上第一笔订单,每天睡觉的时被压缩到4个小时。
打零工看似时间自由,但他们却陷入更大的系统中,无法停下,王聪察觉到一旦佛系对待抢单,事后的订单质量会大打折扣,比如系统分配的订单配送金额偏低,匹配的送货点较远,“如果连续三四天不跑,基本上就没单子可以接了。”
在这个无形的系统里,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陷入了更无感的关系中,“平台-个人”这一形态决定了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雇佣关系,这被统称为零工经济。
根据2020年政府公开数据,国内零工经济大概能容纳2亿人就业。这2亿人的生活状态就如罗振宇口中“U盘化生存”,做一个U盘,可以自由地接入组织的接口当中。
平台经济时代的到来,使流动劳动成为常态化机制,稳定、固定的社会信念基底正在瓦解。
58同城招聘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灵活用工市场研究报告》可以发现,2亿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扩大,2020年前三季度灵活用工招聘需求占比21.91%,近几年全国灵活用工求职需求呈快速上涨趋势,平均同比增速超40%。
2020年前三季度,灵活就业求职者中,90后与00后占比超过一半。从学历来看,高中及高中以下求职者占比58.49%。
零工经济下的2亿劳动者开始被描绘出一幅画像,他们小小年纪就被叫作师傅,快递师傅、外卖师傅、司机师傅……


中国零工经济活跃行业和薪资,图源:58同城招聘研究院
以90后、00后为主的小镇青年,大多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是中国互联网时代下的“原住民”,对于互联网经济催生的新业态、灵活性具有较强接受度,但并不将此作为一份终身事业,他们仍打算回老家结婚生子、落叶归根,于是对社保无感,被平台和系统推向了一个不安全的境地。
到手更多的钱,时间自由,进入门槛低,往往是选择打零工的初衷。
在上海8年,王聪靠送外卖、打零工还清了老家的房贷,最近,他还实现了出行自由,一辆丰田凯美瑞出现在他朋友圈。
“能拿多少养老金和意外险都是后话了,短期能赚到钱才是最要紧的”,每个月1.5万元左右的收入是老家工厂4个月的工资。去一线城市送外卖是他最不后悔的决定,尤其是当他如愿坐上新车驾驶座的时候。
打工人看似有了更多元的选择,更自我的意识觉醒,但他们仍在更大的社会系统里内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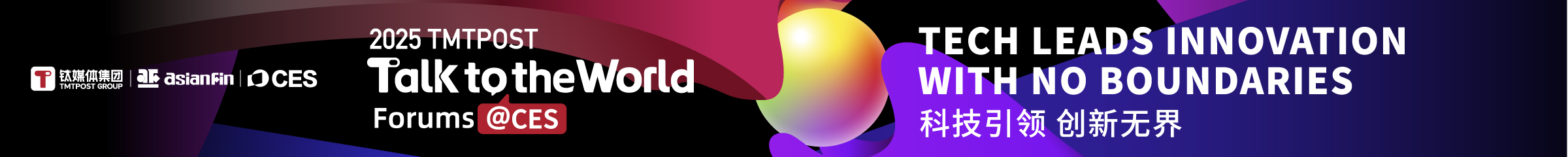

 快报
快报
根据《网络安全法》实名制要求,请绑定手机号后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