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降噪NoNoise,作者 | 阡陌
01 价格
「没有足够的收入,生活的希望就被截去了一半。」
这是毛姆在1915年首度出版的小说《人生的枷锁》中写下的句子。107年后,当他的中国粉丝、30岁的舒婷站在满是荒草的工地围墙边,巴望着工地上写满编号的各式工程车,期待找到自己新家大概位置时,这句话,突然就从她脑子里冒了出来。
舒婷很快把它变成了更符合自己当下情况的版本:没有足够的收入,生活的希望就被截去了一半,连房子也要飞走了。

舒婷在2022年2月签下了那份购房合同。那是她看过的第三个楼盘,因为户型好,她一眼就看中了。五环外,总价800万,听售楼处的中介说,房子很抢手,开盘第一天,好楼层就被抢空了。最终,在这个高层住宅小区里,她只买到了2层。
「也不错,比1层强」,她安慰自己,小区开发商是业内头部,绿化应该做得不错,到时候,从家里就能看到窗外郁郁葱葱的绿荫,清晨或者傍晚,阳光透过树叶洒进来,没准,会美得像油画一样。
茨威格说过,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这套房子并不能算舒婷收到的礼物。320万的首付,是掏空了两个家庭六个钱包,再加上跟朋友借了50万,才勉强凑齐。从数学意义上,这套房子的售价是800万(算上贷款利息,接近1000万),但它暗中包含的价格,远不止于此。
比如,自由。
这曾经是舒婷最看重的东西。从清华毕业后,她没有像同专业的大多数人一样,选择公务员、稳定的国企或者金融机构,而是加入了一家 NGO 组织,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拓展眼界和知识。她经常出差,去到一些此前连名字都没听过的山村,与孩子们在一起时,她身心都是自由的,所有的劳动,也是富有价值和意义的。
这样的日子过了5年后,她去了西二旗的大厂。
她对大厂充满好奇。她所在的岗位,与教育有关。以松散的方式工作几年后,她也渴望在高效运转的互联网系统里,得到更好的锤炼。另一个直接的原因则是,她结婚了。当考虑事业和生活的立场不再只是个人喜好和感受,选择的结果,就可能与过去发生偏差。
回头来看,这两次职业选择的底色,都有着相似的自由。想做的事情就努力去做,哪怕失败了,也不用后悔。这是写在东北女孩骨子里的DNA。
不过,签下购房合同的那一刻,舒婷清晰地感受到,有些东西,就此在售楼处的香氛和音乐中,碎掉了。
未来30年里,她要承担每月2.6万的房贷。她和老公都在大厂工作,两人收入加起来,平均每月是税后5万。她清楚,在北京这座城市里,这样的家庭收入,只能算中等。而背上房贷就意味着,在接下来的30年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失业——除非其中一方的收入,出现了质的飞跃。
这是一种弦被拉满的感觉,在房贷清空之前,那只看不见又强有力的手,会一直紧紧捏着那根弦。
弦,在2月末又紧了紧。舒婷看完工地的一周之后,28岁的字节跳动程序员猝死在健身房,留下怀孕2个月的遗孀,这位被坏消息击中的年轻妻子在买房群里发问,如何可以办理退房退款,因为每月两万多的房贷,她靠自己,无力承担。
兔死狐悲的情绪,在那晚将舒婷包围。一位字节跳动员工也匿名感慨,虽然不认识去世的吴同学,"但物伤其类,看到他妻子在心碎时还要考虑钱、孩子等现实问题,我有一种照镜子的感觉。"
02 流水线
我们沿着铁轨奔跑
进入一个个名叫城市的地方
出卖青春
出卖劳动力
卖来卖去
最后发现身上仅剩一声咳嗽
一根没人要的骨头
这是90后富士康诗人许立志生前写下的诗。他在富士康发生13连跳之后的2011年,坐在了流水线上。3年后,他从17楼一跃而下,留下193首关于打工人的诗。
在大厂集中的西二旗,上下班高峰时的地铁口、公司食堂,总涌动着黑压压的人头。所有人都穿着类似的衣服,冬天是膨胀的暗色廓形羽绒服,夏天是各种颜色的T恤衫,加上口罩和工牌,若从他们身边路过,你能留下的印象,除了工牌上的公司名字,大概率就没有其他了。
等坐到被玻璃幕墙包围的工位时,他们又变成了花名和 title,融入繁复的项目中,如同流水线工人一般,机械维护着这套系统的运转。
「大厂」,当越来越多的人习惯用这个词形容头部互联网公司,它们与富士康流水线的相似性,已经跃然纸上。
29岁的康康,并不认为自己比同村那些在富士康工作的女孩强多少。「都是吃青春饭」,她已经有了颈椎病和腱鞘炎,这几乎是公司最高发的职业病,除此之外,就是脂肪肝、高血压和高血糖。它们出现的原因各异,共同点是都与久坐有关。
康康已经很久没去健身了。她现在唯一的娱乐活动,是在微博里写搞笑段子。那是她的另一面,在公司,她鲜少展示。妆后的她酷似漫画里的美少女,但上班时,她也懒得装扮,一件T恤穿3天,是常有的事情。
「流水线上的女孩,不配拥有美丽」,她自嘲道。

有时候,她甚至会觉得自己还不如富士康女工。女工们换工作的机会成本很低,只要技术够熟练,不愁找不到工作。但在互联网公司不一样,每天都有履历更优秀的年轻人加入进来,他们有更灵活的脑子、更能熬夜的身体,随时可能取代掉她。
进入这家公司4年,她在经历周末不得不爬起来去开会,听领导PUA的时候、经历推进项目遇到其他部门不配合,明明是同级,还要舔着脸去说好话的时候,总有「老娘不干了」的冲动。但在找到下一个坑之前,她不敢。
尤其在裁员潮席卷互联网公司的当下。
她加了很多同行的微信群,隔三差五就有人在里面讨论裁员和找工作。焦虑,就像西二旗那些大厂的办公楼灯光一样,不分日夜地点亮着。
对失业的恐惧,有很多是源于房贷。每个月的10号,她都要往房贷银行卡打1.2万。3年前,她在厦门买了房子,首付是父母出的,房贷由她来还。她打算在北京工作几年,将来搬到厦门去定居。这份月薪两万的大厂运营工作,至少能让她顺利供着房子。
只是,康康总觉得自己不是在打拼事业,而是在为房子打工。
想离开又不知去向何方,被迫离开者,则可能陷入窘境,这是「大厂人」的宿命。
37岁的黎明在10年前通过考公,逃离了这种宿命。他从深圳一家互联网大厂离职,顺利考上市属公务员,过着薪水不多、工作繁忙但压力不大的生活。去年,他接到前同事的电话,对方突然被裁,家里供着两套房的房贷,养着两个娃,妻子没有工作,想借几万块钱周转一阵。
他拒绝了。这位前同事有借钱不按期还的历史,他不愿去为这种人担风险。
在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高价值的房子,是外来者的底气所在。这些满怀信心的「大厂」年轻人,在买下房子的那一刻,憧憬着的多是幸福和美的新生活,以及房子增值后带来的身价上涨。
但在很大程度上,这是过去那个互联网欣欣向荣、房地产大跃进的时代所创造的红利「幻影」。有人很幸运,在「幻影」破灭前,完成了从财富、身法到阶层的跃迁,有人直到站在危险边缘,才发现「幻影」已经破灭。
2017年,在华为工作8年、中兴工作6年的程序员欧建新在被中兴劝退后,选择了跳楼。42岁的他,留下四个老人、没有工作的妻子、分别9岁和2岁的孩子、以及没有还完的房贷。没有人知道,这个家庭后来是如何继续生活的,有没有留在深圳。
03 时机
人类的悲欢不是总能相通,同样的路径,也可能通向完全不同的终点。
在买房这件事上,舒婷补上了「时间成本」这门课。大学刚毕业时,班里有同学依靠家里支持,贷款在回龙观买了房,每月房贷6000块,她私下表达了不屑。
8年之后,那套房子的价值接近翻番。随着收入的上涨,每月6000块的房贷,对那位同学而言已经毫无压力。关键是,她免去了「北漂」租房的磨练。
关于时机的重要性,命运总会让年轻人慢慢明白。
比如,同样在互联网公司工作,十年前跟现在,意味着完全不同的境遇。「再干几年,45岁就退休」,舒婷记得,那位师兄说出这番心愿时,满脸云淡风轻。他当时是一家准备上市的互联网公司副总裁,在此之前已经在某头部互联网公司实现了财务自由:美股账户上有近千万美金,北京两套房,无房贷。
舒婷后来总结,这些在财务上取得成功的「大厂」人,具备两个共同点:
首先,他们在对的时机,进入了对的公司,坐上了对的位置,在公司业绩或者上市红利之下,积累了足够多的财富。其次是买了房,并享受了房产增值带来的红利。
但随着互联网行业的风雨飘摇,那些依附于它的光环,也在摇摇欲坠着。33岁的晴子和老公都是互联网「大厂」员工,2020年,趁着疫情房价低点,他们卖掉了传媒大学附近60平米的老房子,在天通苑买了140多平的大户型。
超过140平米,意味着这是非普通住宅,在首付和房贷方面,都要相比普通住宅门槛更高。两人没凑够钱,最后只能申请了60万的消费贷,每月还款2万多,3年还清。
多年积蓄被这套房子掏空之后,全家过上了缩衣节食的日子,婆婆炒股收入不错,主动承担了家里包括孩子在内的所有生活开支。
「我老公每天早上6点半出门,晚上经常加班到十一二点才能回来」,晴子说,老公今年36岁了,赶上这两年大厂动荡,更加没有安全感,总担心哪天自己被裁掉。他们现在在想尽办法攒钱,以备将来万一失业,不至于房贷断供。
他们都享受过「大厂」的风光,不管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比如公司大方派发的股票、丰厚的年终奖,抑或是,亲友聚会聊及工作时,收到的那些羡慕眼神。
在北京这座城市里,互联网是过去十几年里发展最快的、释放红利最多的行业。在上行周期里,乐观的情绪曾经环绕在「大厂」的每一张工位上。年轻人都相信,只要投入更多的时间,付出更多的努力,就能收获更好的回报。
这是一个确定的公式。中间没有太多变数。
如今,数字被打乱了,新的解题逻辑还在建立中。经历过起伏的「大厂」中年人已经在规划撤退方案,比如那位计划45岁退休的互联网高管,比如晴子一家。她想好了,再攒几年钱,等房贷压力再缓缓,就让老公去找份国企的工作,挣钱少,但胜在稳定。
而更新一代的年轻人,已经不再仰视「大厂」了。他们也不再迷信这些成功创业者的鸡汤故事,当变革的大潮汹涌而来,他们更愿意转身,争取那张更庞大稳定的大船的船票,比如,公务员。相比在一线城市奋斗,回老家,成了更被年轻人接受的选择。友好的房价,在其中功不可没。
早来的,财务自由了;晚来的,选择自由了。只有中途上岸的这波「大厂」人,背着房贷,在内卷的游戏里继续战斗。而多数人的努力,是为了有朝一日能「离开」。
徐立志在诗里描写过类似的感受:
我想在凌晨五点的流水线上睡去
我想合上双眼
不再熬夜和加班
此行的终点是大海
我是一条船
他最终化作一叶扁舟,驶向了无边暗夜。
而对于还在「海上」漂泊之人,希望是最明亮的灯塔。从工地回出租房的地铁上,舒婷翻起了家装攻略。她已经开始规划,灯要如何布置?买吸顶灯还是全屋无主灯?客厅要放电视还是投影仪?
她想好了,等待房子交付的这两年,要更加努力地去工作、挣钱、攒钱。实在疲倦或者烦躁的时候,就来工地转一转,用「家」的进展来自我治愈。毕竟,只要人还在,希望总是会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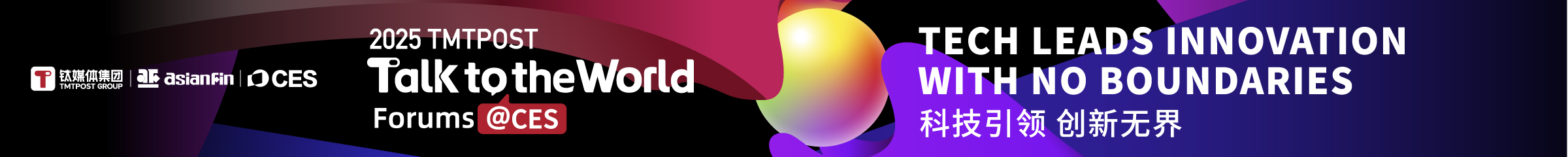

 快报
快报
根据《网络安全法》实名制要求,请绑定手机号后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