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众面,作者|杨灏楠,编辑|胡展嘉
有一批人,他们是年薪百万的高管,在社会上享受着大厂光环,但公司里却没人知道他们的真名;他们花几万买实习挤进大厂,为了钱或者“职业发展”,出卖姓名,成为竞对公司里的间谍员工,早就把姓名抛之脑后。
在Apple出品的神剧《人生切割术》里,主人公马克被切割成两个人格:公司人格和日常人格,从他踏入公司电梯的那瞬间,他的日常人格就会陷入沉睡。两个人格互相独立,记忆切割;同时他们名字不一样、性格不一样、想法不一样,也不知道彼此的生活。
在太平洋这侧,中国互联网大厂正在试图把《人生切割术》变为现实。谁赋予了互联网公司这样的权力?社会身份该不该在大厂这部精密运转的仪器里,被重新定义?被隐去姓名的年轻人去大厂的意义在哪里?这是被同化还是被异化的魔幻现实?
众面不久前,也和大厂里的年轻人聊了聊,他们被隐去姓名的大厂岁月,对他们的人生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01 “直到老板被抓走,我才知道她叫什么”
直到老板在工位被抓走,张杰才知道相处一年的老板真名叫什么。
张杰没有误入什么传销组织,是在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做运营。老板涉嫌职务贪腐,而当她的真名出现在内网通告时,张杰只觉得陌生,因为无论是工作时的“花名”,还是她自我介绍时讲的“真名”,都不是盖着红戳的文件里的那个名字。
老板来自于竞对公司,为了躲避前司HR们的“猎捕”,从入职那天起,就设定了无数个假名和“假动作”,以此掩盖在这家公司上班的事实,毕竟,可能在那份秘密协议里,泄露后的违约金是现司要赔偿给前司的。
在包含假名的设定里,一切都变得不真实起来。
张杰知道,这个女人大概30多岁的年纪,有些发福但是似乎很在意身材,她好像处在一段关系中,但说不准到底是男友还是老公;工作上,她常常吹嘘在上一家的业绩,但是从公司下班时,却需要戴着帽子口罩,从B1车库开车走出公司,防止前司偷拍。
她没有工卡,不能在食堂吃饭。
她出门戴口罩、眼镜,像明星一样提防狗仔。
她像工蚁,把自己的经验从一个厂搬到另一个厂。
在张杰看来,老板这些反常现象,都是现司帮助躲避前司“取证”的手段。没有工卡吃饭,就没有在这个厂的消费记录;用“花名”或者是其他假名,就没人知道他们真实的一切,包括前司,唯一知道真相的人只有自己的老板和HRBP。
与此同时,前司的HR们其实或多或少也知道一些这些离职员工的去向,信源包括但不限于同事们的八卦、寄给该人的快递,匿名电话等方式,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这场猫鼠游戏往往有期限,最短的半年,最长的一年。在这段时间内,离职员工会照常收到一份前司的“竞业金”,通常是工资的30%~50%。因此,在有巨额成本的情况下,能得到这种竞业待遇的往往是一些中层以上人物。
在竞争激烈的同类型公司内部,比如阿里、字节、B站、小红书、快手,你会发现某个部门从老大到员工,有一半的人都用假名。这种互相挖墙脚的行为,在过去两年竞争激烈的领域并不少见。对于已签订竞业协议的人来说,在竞业期还要冒着吃官司的风险入职竞对公司,也是艺高人胆大。
“大家都这么干,没关系的。”张杰的老板入职时,HR这么跟她说。这位年薪百万的大厂中层也有自己的苦衷,在这种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不可能靠着微薄的竞业金坐吃山空。
为了避免“出事”,老板们也是煞费苦心。张杰的老板在大厂里没有“关系”。她的微信里没有女老板们爱发的花朵和自拍,朋友圈仅三天可见,也没有任何“装修”痕迹。午饭后,大家一起AA,只有她会请同事帮忙代付,然后拿出一张现金来。
某次,老板拿出自己前司的PPT给大家看,张杰从水印上能看出来她好像叫张XX。但张杰也不知道她到底是姓张还是姓李,总之张冠李戴,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份互相保守秘密的氛围。
下属们一般不会讨论竞业老板的事情。毕竟,如果自己害人失去工作、赔付高额赔偿金,可能变成对方一辈子的仇人。
自然,下属也不能知道老板的风评。一位新同事入职前想要打听一下老板的风格,张杰帮他在内网搜了一下,发现搜不到这个人的名字。等到同事来了,才发现人还是那个人,只是又换了个名字。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在瓦解。
不少公司开始实行“全员竞业”,除了外包和实习生,员工们都要跟随劳动合同签署一份“竞业协议”。2021年8月,长城曾因为一份超长的竞业协议企业名单引起关注。根据这份协议,离职员工在协议有效期内不能入职的企业多达130家。互联网公司里,一旦你被一家竞业,可能连外卖小哥都做不了——某东、某团,都是竞业对象。
这种背景下,人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姓名、关系,“隐姓埋名”进入一家新公司上班赚钱。只是走了之后,本该积累的人脉关系,却因为竞业而变得“避讳”——毕竟你不知道谁会“举报“你。
张杰离职后,曾经给老板发过信息,只有一句话:老板,你叫什么呀?而那个微信,早就停止了更新朋友圈,也没有回复过他这句话。
02 “被迫失去姓名后,我成为公司的工具”
在某些大厂里,新员工入职第一天就会被要求改一个“花名”,将其作为自己在这家公司的姓名。
这个制度从阿里开始兴起,创始人马云把“花名”制度套上武侠小说色彩,给自己起名“风清扬”。这是金庸小说《笑傲江湖》里的角色,熟习独孤九剑,剑术超凡,隐居在华山后洞。一个花名不仅代表着你的喜好,也代表你内心想成为的那个人。
不过,在漫长的治理过程中,花名却慢慢变成一种对员工的伤害。
离职后,如果想取证,由于在办公软件、微信都使用花名,维权会存在取证困难。除此之外,花名也成为了一种身份的象征,在阿里,三个字花名的人就是比两个字的人入职时间更早、职级更高;花名制度也让同事们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每天在公司见面的人,你其实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名是什么,虽然真名就在花名之后里用一个小括号写着。
在《人生切割术》里,Helly也是入职后才拥有了这个姓名。下了班,她并不知道“Helly”是谁。失去姓名之后,员工的工具感更强烈了,因为没人注意到“你是谁”。
在奉行“培养员工”的大厂里,应届生徐天却没觉得自己得到应有的“尊重”,首要问题,就是她失去了24年拥有的姓名。在这家年轻的电商公司里,她一边体会着新鲜,另一边用另一个名字来承受老板的“PUA”。
会议室里,老板说:“莎翁,我对你的期待是12分,现在你连5分都没做到。”她恍惚间,觉得老板在骂另一个人,可笑的是,她取这样的花名也只是因为她喜欢莎士比亚的戏剧,但是莎翁本人的职业生涯却是顺风顺水。
在大厂里,经常出现这样的闹剧,但是唯一不变的是:员工碎了一地的尊严。
时间久了,徐天觉得自己就是莎翁,在公司外,偶尔听到“莎翁”,也会不自觉地心头一紧。“这个反应应该是人训练出来的吧?狗狗得到一个新名字,很快也会随叫随到。”徐天说这话时,边喝酒边表情惆怅,似乎自己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被随时收养在不同家庭里的小狗。
花名,似乎是公司对一个人首次宣布“所有权”。还记得当时选花名时,徐天想了好几个名字也没有被HR通过,包括但不限于在世名人的名字、影视剧里的人物,提交了7、8个名字,要么和现有或者历史上的公司人名读音相同,要么就是HR不允许。擅长搞怪的她,在想到崩溃后,把《家有儿女》里的角色名字作为花名备选项。
HR看到这个名字在审核中,特意跑来问,你觉得,你叫“姥姥”,你老板、CMO都管你叫姥姥,合适吗?可笑却也很无奈,在所谓可以自由称谓的互联网公司里,所有的自由有条件且隐形。小徐最后选择了中规中矩的“莎翁”作为花名。
成为“莎翁”那一刻,就像螺丝钉焊接到机器上,工具人属性浓烈,同时,意味着平行世界里的另一个自己,已经和大厂牢牢绑定。
03 “离开大厂,拿回姓名,做回自己”
在林浪眼里,他早就有了上班和下班两套人格了。
“已经有三年,公司里的人,没有人叫过我真名了。”他说。不过这不是最惨的,有些同事的花名取得不好,很像那种两个字姓名。他同组的同事叫李格,不少跟他对接的同事以为他姓李,有天林浪跟“李哥”下楼抽烟,李哥突然问他,“你知道吗?我不姓李。”林浪愣住了下,“啊?你竟然不姓李,那你姓啥?”李哥一笑,说真名姓马,两个人哄堂大笑,边笑“李哥”边说,这上个班连自己姓啥都不知道了。
这样的日子过久了,林浪决定离开大厂。成为了真正的自己后,也把微信名从花名改成本名。有不少加了微信的同事第一句话说,原来你叫这个啊。
不过三年大厂生活,也让他颇觉不真实。除去姓名,他跟同事们并没有成为“真实”的关系。随着内部账户被禁用,他也消失在一些不相熟同事的世界里了。不过,偶尔在自己的社交软件上,他会跟女孩用花名介绍自己。仿佛这样约会的时候,他可以用另一个人格应对。
在新公司里,叫回本名的林浪一开始还不习惯,他甚至不那么好意思在会议室开怼了,仿佛之前花名时代里,他的出言不逊能有一个莫须有的罩子挡住真实的自己。在和同事说一些事情,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仿佛变得慎重了许多,因为PPT和文档里最后的名字,是自己携带了20多年的真实人生。
与此同时,公司“内部”和“外部”界限也在模糊,他和公司里的同事们也会闲谈一些家里的事情,周末相约去爬山。他感到现在的生活才是真正的“Work Life Balance”。
在聊天最后,林浪突然想起来在自己的小学,很不愿意写名字,暗暗发誓一定要改一个“好听的、像王子一样的”名字,很多年后他重获了这个权利,但却让他最终逃离虚假。
大厂赋予人们金钱和相对的“机遇”,却也抹杀了作为个体的“自由”。有人觉得上个班而已,别人叫自己什么都可以,但是某些时候,连名字都抛弃的人,或许也不再是自己。或许,花名并不是方便员工的,而是方便老板的。这,或许就是你被要求“隐去姓名”的真相。
(备注: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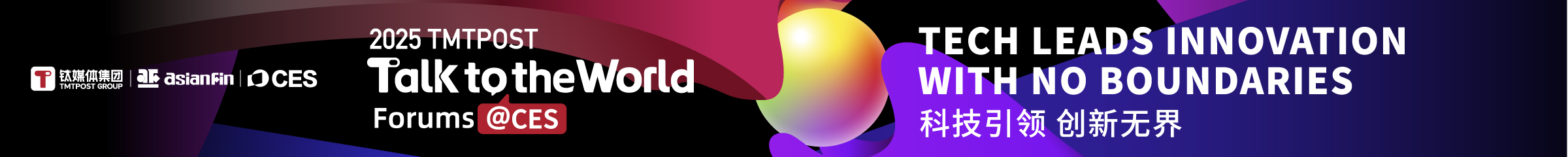

 快报
快报
根据《网络安全法》实名制要求,请绑定手机号后发表评论
那就起个“我最屌”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