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钛媒体注:本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九行Travel(ID:jiuxing_neweekly),作者 | 张海律,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新西兰旅游,为什么常年火爆?
或许因为这里是魔戒拍摄地,这片群岛上同时拥有火山、温泉和冰川;
或许是因为这里的奥克兰的城市生活很宜居,而皇后镇的高空极限运动很刺激;
或许是因为这里看似远离世界中心,却依然发达殷实,还有可爱的Kiwi鸟。
在新西兰2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500多万人口,他们是毛利人、英国人,再到后来的欧洲人、东亚人、南亚人、美洲人……
这些来自不同族群的人是为了逃离战争、改善生活、退休享福种种原因来到这里,却用一百多年的时间,共同谱写了新西兰最美的风景和故事。
财经杂志《福布斯》曾评选出“全球最友善国家(The World's Friendliest Countries)”,新西兰各项指标均获高分,荣登首位。其原因,也大抵在此。
怀唐伊,一个国家的诞生
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大英博物馆推出“晚清百态”特展,首次将文物《南京条约》摆出来展览。与此同时,远在大英帝国前殖民地新西兰的我,走进该国最大城市奥克兰的博物馆,在一个转角见到副标题为“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而共同生活的象征”的《怀唐伊条约》(Treaty of Waitangi)常设展。
这是一份对新西兰历史、宪法和民族融合至关重要的文件。
1840年2月6日,作为英国王室领事的威廉·霍布森上尉和来自北岛43位的毛利酋长首次签署该协议。协议经亨利·威廉牧师翻译成毛利语版本,随后在各部落间传播,并由各自的族长陆续签署。这让新西兰成为受英国王室保护的殖民地。
《怀唐伊条约》的签署,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北岛一些毛利部族的共同请求,他们担心法国人入侵,因而请求维多利亚女王给予保护。
由于民族文化和语言体系相距甚远,最初的《怀唐伊条约》在很多重要条款上远远没法做到准确翻译,需要在历史进程中不断修补这些有意无意的误会。
我驱车北上,来到位于岛屿湾(Bay of Islands)岸边的国家历史地标怀唐伊(Waitangi)。下午3点,正赶上每天的最后一场毛利文化演出,于是径直往前跑了好远,跑到这片偌大领地尽头的一座雕琢精美的毛利议事厅(Te Whare Rūnanga)跟前。
迎海的大草坡顶,立着一根34米长的旗杆,上面悬着1834年一些酋长形成联合部落以来,新西兰历史上的三面不同旗帜。几个精壮的毛利汉子,迎着秋日的海风,裸着上身,手持长矛,跳着著名的毛利战舞,一步步逼近站成一排的观光客。
这是我第一次目睹毛利传统习俗。不知道183年前代表英王室抵达这个海湾,准备签署条约的威廉·霍布森上尉,是不是见到了同样一番文化奇景?
穿插着情绪饱满的战舞,将人体作为一件乐器进行有节奏地拍打,伴着吉他弹唱的多首歌谣……相信这其中既有仪式习俗的延续,也有旅游业带来的娱乐需要。
相较于在强势而霸道的文明到来后,迅即被降维打击到几近灭亡的其他原住民文明,毛利文化从来算不上弱小,他们比地球上其他民族更早掌握了远洋航海技术。
怀唐伊博物馆刚过入口处,用两侧等比例排开的画卷拉开了这一南太平洋神奇岛国的人类历史帷幕。
左边,是毛利人先祖驾驭过的独木舟,通过这一没有罗盘的交通工具,一千多年前,波利尼西亚人库普抵达这块除了蝙蝠再没有其它哺乳动物的土地,南岛语族陆续从太平洋各地航行而来,建立了繁荣的社会, 繁衍数百年;
右边,是高大帆船引领的欧洲地理大发现,荷兰人阿贝尔·塔斯曼、英国人库克船长和更多的后来者,陆续“再发现”并进一步开拓了毛利人的岛屿。

毛利人与欧洲人先后抵达新西兰。/摄影:张海律
两者文化观念相距甚远,对土地的理解也有着根本差别:毛利人认为不同族群都隶属于土地,而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只是将土地视为可以拥有和交易的商品。
这也导致《怀唐伊条约》从第一条——“新西兰联合部落邦联的领袖和其他还未参加邦联的独立领袖,必须绝对而毫无保留地把他们所有的主权权力让予英国女王陛下”——就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
毛利人并没有主权概念,“主权”一词无法准确翻译成毛利语,只能译为“kāwanatanga”,是英文“governorship”的借词,表示“治权”。
在1840年,除了极个别频繁与英国人做生意的部族酋长外,其余从未有被政府管治经验的毛利部落,很可能只会认为自己是在与英王室分享权力。总之,在误解和妥协中,一个暂时属于英殖民地的国家诞生了。
从毛毯到橄榄球,毛利人为何而战?
《怀唐伊条约》就是在最早定居者詹姆斯·巴斯比家的客厅签署的。如今,这幢历史建筑翻修一新,就在毛利议事厅旁。
当时,绝大多数毛利部族酋长没有签字,有些是还没看到利益所在,有些则是没被通知到——整个南岛只有4个部族接到了邀请。
43位或多或少懂点英语并首签条约的部族酋长,获得了来自英国王室的礼物。Tuwharetoa部落酋长是兄弟二人,弟弟去怀唐伊签了字,位高权重的大哥则坚持让弟弟把礼物还给英国人。
条约的签订,让部族间战争——因欧洲火枪大规模到来及交易,形成军备竞赛和冲突——暂时消停。但更多源自土地纠纷的剧烈冲突,陆续在英国人与毛利人、来自欧陆的新殖民者与毛利人,以及毛利部族间爆发,史称“新西兰战争”,从1845年延续到1872年。毛利人口在这些年间急剧减少,从条约前的10万缩减到6万,和欧洲定居者人数相当。
今日的怀唐伊领地,还有一座名为“公民身份代价”的博物馆。
该馆从入口开始,就引领参观者思考:协议之后的英国人,是统治者还是最初声称的合作伙伴?并回溯近现代史上毛利人参与的历次战争——从南非布尔战争、一战、二战、朝鲜战争、越战到当代维和行动,如此设问:“被统治的毛利人,干吗要去地球遥远的另一边,打一场和自己民族毫无关系的战争呢?”
原因很多,展馆也并不试图引导出一个答案。在一座被战士黑白遗像纪念墙环抱的肃穆建筑上,写着一句诗:“他们已不再变老,年龄不会让他们疲倦,岁月也不再为难他们。”

毛利战舞表演。/摄影:张海律
二战前,因世界各地移民的到来,新西兰人口增至160万,毛利人仅有9万,占总人口的5.6%。到了2018年,有毛利血统的人口达60万,占总人口的16.5%。
二战时的毛利营副官乔治·伯特,有一名孙辈叫兰乔治·娜拜尔,其人在上世纪末工党领导的全方位平权运动中,于1995年赢得地方选举,成为北岛南部怀拉拉帕(Wairarapa)第一位毛利人市长,以及全世界第一位公开的变性人市长——是的,他成为了她。
娜拜尔于今年3月去世,她插着毛利头饰的肖像,进入奥克兰美术馆,成为毛利文化展馆及LGBT的代言人。
从建筑标识到博物馆内容展板,如今都用英语和毛利语呈现;驱车进入奥克兰南面的怀卡托(Waikato)和丰盛湾(Bay of Plenty)两个大区,电台传来毛利语的音乐和新闻节目。
新西兰国民中,无论是欧洲白人、华裔、印度裔,还是来自太平洋其他岛国的移民,或多或少都能说上几句毛利语。
在罗托鲁瓦(Rotorua)一处火山带地热区,村庄向导自豪地指着墙上那37个字母,让游客跟着学习朗读:“Te Whakarewarewatanga O Te Ope Taua A Wahiao,这已经是够短的毛利地名了,意思是‘战斗派别聚集地’。这里是新西兰观光旅游尤其是向导行业的发源地,很可惜我的那些前辈不能说甚至不会说自己的语言。”
确实如此。曾几何时,在学校和公开场合是禁止说毛利语的,而新世纪政策180度的大转弯,让毛利语成为全世界几乎唯一彻底复苏,甚至变得更强势的原住民语言。在一户原住民家庭中,很可能长辈不会说毛利语,反而是学龄孩子会说。

毛利向导教游客读出漫长的地名。/摄影:张海律
天黑后,到这片地热区另一面、同属一个家族的蒂普亚毛利文化村(Te Puia)参加晚宴和文化体验活动。蒂普亚是新西兰毛利工艺艺术学校的发源地,也是南半球最大的间歇泉——波胡图(Pohutu)所在地。
围着一桌美味的陌生客人,除我之外都来自澳大利亚各地——悉尼、墨尔本、昆士兰、帕斯……他们也惊讶于毛利语恢复得那么彻底:“简直就像英国人最初来到这块土地一样。虽然历史发展差不多,但这在澳大利亚就不可能,主要原因还是我们原住民部落太多了,彼此之间无法用共同语言交流,而新西兰几百个部族都说一样的毛利语。”
夜空之下,在参观持续喷涌的壮观热泉时,我问毛利女向导:“你们的文化和语言恢复得那么彻底,甚至变得更强势,除了政策倾斜外,还有别的原因吗?“
“因为我们毛利人非常骄傲,而且占有欲极强,没人能从我们这儿拿走任何东西。另外就是,我们对橄榄球贡献巨大。”女向导回答道。
我在奥克兰参观全黑队体验馆(All Black Experience)时得知,超过半数的国家橄榄球队队员有毛利血统。这是一项对移民国家的精神和凝聚力最为重要的运动,能加入全黑队,跳起毛利战舞,意味着至高无上的荣耀。
更衣室里,队员们说起接到录取通知的情景。一个白人小伙第一时间打电话给热恋中的女友,却沉默了半分钟开不了口,女友着急哭道:“怎么,你要分手吗?”一个毛利女孩立马上车,去通知最热爱全黑队的父亲——不过是到已经阴阳两隔的墓地。
进了全黑队,不管是毛利人还是其他族群,才是真正全身心地为新西兰而战。
广东江门的那些好男好女
虽然《怀唐伊条约》是英国王室和毛利人签订的,但近两百年的移民史中,共同组成新西兰这个国家的,远不止英格兰人和毛利人。
海事博物馆入口,我随机抽了一张名片,成了3岁的苏格兰女孩Jane,在1846年随全家登上运兵船“东方皇后号”,睡在逼仄的三等舱,颠沛流离几个月,来到父亲将要驻防的新西兰。
那个渣男退伍后,抛家弃子去淘金,“我”和母亲因生活所迫,开了一家妓院,被抓进监狱。半年后,“我”在牢里死于难产,年仅23岁。
这样的悲惨故事,在最早的移民群体中很普遍。随着交通科技的发达、社会的发展,以及更为重要的移民原因变化,这些故事变成书本里的记忆。
远走他乡的原因,从最初苏格兰的高地清洗、爱尔兰的土豆歉收和广东人被“卖猪仔”来淘金,变成二战时波兰人逃离战火、二战后荷兰人的农垦种植、南亚人的改善生活,以及全世界老人的退休享福。
可惜的是,我们能在博物馆和文献库里查阅到来自欧洲、有名有姓的越洋故事和家族脉络,却极少能看到华人的名字。

19世纪初移民远洋船的三等舱。/摄影:张海律
奥克兰战争记忆博物馆最大的一战展区尽头的一个角落,展出了澳新军团华裔军人的故事。
三张黑白肖像照里的詹姆斯·阿诺·王李、昂金·何就、石赤辉,与加入一战战场的其他33名华裔一样,几乎全是中英混血儿,且大多是父亲来自广东江门,母亲来自苏格兰或爱尔兰。
参军人数只占1916年登记在册的新西兰华裔男性人口的1.8%,且全数来自以农垦和矿业为主的偏僻城镇。首都惠灵顿当时的286名华裔男性,则没有一个人服役。展览说明文字认为,这些小镇青年,与白人邻居共同生活,和学校小伙伴相伴成长,更容易认“英”归宗。
虽然广东男性自1860年就到新西兰奥塔哥淘金,但女性一直留在家乡。1881年,新西兰的华人男女比例为555:1,也就在这一年,新西兰政府通过《中国移民法案》。此后53年,新西兰针对中国移民征收节节高涨的人头税,并严格限制每艘船只的登陆人数。直至2002年,新西兰政府才就人头税的不公正式向华人社区道歉。
抗战时期,陆续有广东女性来到新西兰,与丈夫或父亲团聚。这其中就包括奥克兰艺术家Bev Moon的祖母和母亲。
我在北岛北部城市汉密尔顿(Hamilton)一座博物馆的最后一个展厅,认识了这位艺术家,并震撼于她“做”出的一席丰盛粤式茶点。
1940年1月23日,Bev的祖母李彩贵带着7岁的女儿叶彩贵,从江门台山乘船来到惠灵顿。母女俩受教育程度都非常有限,却在男人打拼出来的唐人街,通过下厨和针织这两项精湛技艺,最大程度地补贴了家用。
在新西兰出生长大的Bev,受过高等教育,成为知名艺术家和画廊经理。疫情封城期间,她挂念已故的祖母和母亲,结合母辈这两项技艺,用通过网购而来的不同色彩、色度、材质的毛线,编织(烹饪)出这一大桌献给台山伟大女性的茶席,祝福她们“吉祥如意”。
好山好水的一座围城
以前住在奥克兰的同学、朋友和远亲,几乎都回国了。这让本是一只无足鸟的我,在从最北的雷因格海角(Cape Reinga)到有着地热奇观的罗托鲁瓦(Rotorua)的旅程中,面对着绝美的风景,第一次莫名地开始想家。
熟人们的离去理由,有为离不开国内社交圈的老人而下决心回去尽孝的,有亲朋好友介绍生意机会的,也有到了一定年纪反而需要热闹和喧嚣生活的。
更多的年轻人则源源不断地过来,补充着紧缺的用工需求。一路上,我见到从马拉西亚和丹麦过来,抓住青春尾巴,通过工作假期挣钱的人;与常居澳大利亚、过来采摘奇异果的山东小伙详聊,对比多边生活的利弊;听印度咖啡店主哀叹自己亏了两年的生意;第一次住进一户华人房东的民宿,听她抱怨奥克兰的拥堵,享受如今生活在北帕默斯顿(Palmerston North)的惬意。最近,在这个小镇里,这个独自带娃打拼的四川女人,收获了第二段爱情和婚姻。
“不是为了孩子能够尽情撒野着长大,我还是愿意待在热闹、好吃的四川。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会问自己:在好山好水的这边生活17年值得吗?直至碰上现在的先生。他在国内生意做得不错,也清楚人到中年的自己想要什么。如今矛盾在于,我想每年有一半时间待在国内,而他因为应酬烦人,只想留给国内两个月时间。”
我们在秋色渐浓的清晨告别。四川女人感谢到她家入住、陪她说说话的我,我也表达了同样的感激之情。之后,继续上路,在好山好水中,探索着这座隐形的围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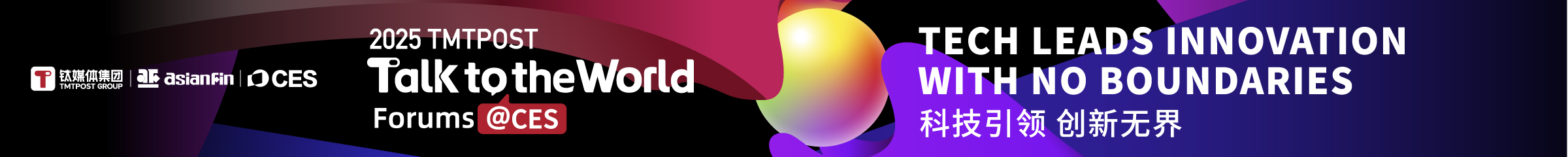

 快报
快报
根据《网络安全法》实名制要求,请绑定手机号后发表评论